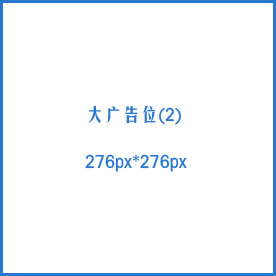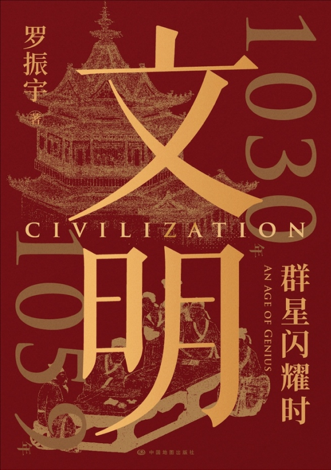 1030年至1059年,北宋仁宗时期。此时的中国,宋、辽、夏各方在边境博弈中达成了微妙的战略平衡。缺乏马匹的宋朝创造了“以远近近”的新战术体系。范仲淹的“先忧天下之忧,而后享天下之乐”重新定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士大夫精神为何在此时觉醒?从刘墉街的歌词到永恒的杰作《岳阳楼》,文学创作为何在此时掀起一股变革的浪潮?宋朝与西夏的历法博弈如何体现技术背后的斗争强度?最近出版的《文明:1030-1059》一书讲述了中华文明在看似平静的30年里在多个层面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嘉佑二年,1057年,是中国科举史上奇迹般的一年。本期共有进士388人。苏轼、苏辙、曾巩、程浩、张载同榜。唐宋八位大师的一半都聚集在这里。”在近日举办的《文明:1030-10》《五十九年》新书发布会上,该书作者罗振宇打开了这段历史切片,聚焦于公元1030年至1059年北朝的“闪亮星辰”。 《挑战与解决方案》图书馆 这些成功、失败、半成功都是宝贵的财富。 “以下内容摘自《文明:当群星闪耀时,1030-1059》,文章中所使用的图画均来自书中。经出版社许可出版。”文明:1030-1059当群星闪耀》作者:罗振宇版本:中国地图出版社2025年11月杜纳行为何重要?1036,这一年,党魁李元浩擒拿一举占领了苏州、瓜州、沙州,垄断了河西走廊,切断了旧地名与同一地产的联系。这个地方因为这场战争,当地人惊慌失措地将大量文件藏在一个山洞里,然后封锁了山洞的入口。这个发现有多重要?可以说,几乎所有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领域都因为这批新材料而被改写。陈寅恪先生对此表示:“一个时代的学术必然有新材料、新问题。用这种材料来研究问题,是这个时代的新学术趋势……出人意料的说不入主流。”换句话说,在20世纪初,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如果不使用敦煌文献这样的新材料,在陈寅恪先生眼中就不属于主流。那么就让我们趁今年党项征服敦煌的机会来问问:敦化为何是重要吗?什么知识分子?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解释呢?我们今天所说的敦煌文化,其实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时间上连续的敦煌,即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另一部分是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另一部分则相反,是被打断的——1036年被雪封存的敦煌文献,一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两部分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先不间断地看一下敦煌。敦煌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岩壁中。从南北朝初年到元末,工匠们执着、雕刻摩崖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现存洞窟735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泥塑、彩绘佛像3000余尊。这么大的尺寸还没有被锁定或收费多年。路过的人们可以随时进来看看。怎么能说是被打断了呢?中国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有一个共同点:都位于险要要道上,靠近路边。例如,云冈石窟位于山西通往内蒙古的一条古道上。所谓“走西口”就是这条路。云冈石窟内还有一处古迹,名为“古路车辙”。龙门石窟尤其如此。地处两山对话处,沂水河夹在其间,犹如一道天然大门。因此,此地又称为“一阙”、“龙门”。古代是洛阳通往关中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石窟分布图。 《文明:1030-1059 当群星闪耀》内页描述敦煌莫高窟怎么样?它地处中原文明通往西域的门户。远古时代,商队走到敦煌,南过阳关,走丝绸之路南道;向北越过玉门关,走向丝绸之路的北线。因此,敦煌自然是一个交通枢纽。古代石窟为何要开凿交通要道?要知道,古人为了开凿石窟,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他们除了砍山、开洞、造像、绘画外,还要培训大量的工人。毕竟,建造一座石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他们在计划什么?目的不是搞艺术品,而是弘扬佛法,积累功德,自然选择人流量大的地点。只有让南来北往的商人和旅人才能看到这个功德一旦他们看到,它就会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敦煌莫高窟为何在元代之后数百年无人知晓?那么敦煌莫高窟为何在元代之后数百年无人知晓呢?因为敦煌已经不再是交通枢纽了。明朝觉得自己的势力无法延伸到西域,所以只封了嘉峪关。我不出来,你不进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贸易逐渐断绝。嘉峪关位于敦煌以东约400公里处。嘉峪关将敦煌隔绝在长城之外,敦煌成为周边部落羊群的聚居地。虽然清朝后来重新控制了西域,但敦煌却成为了一座普通的陆地城市,不再是交通枢纽。不过,莫高窟还在,想看的人可以随时参观。乙即使不看明清以后的时期,单看敦煌从南北朝到元代几千年的辉煌,也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如此多的战乱、朝代更迭、如此多的部落来来去去,敦煌莫高窟如何维护,继续在悬崖上凿洞造像,积累数千年的世界文化奇迹?毕竟它是宗教精神力量的象征。宗教的第一个精神力量就是超越性。因为我们要超越太空,所以我们必须建造一座巨大的佛像;既然我们也需要超越时间,我们就需要用佛像来追求永恒——这种艺术形式太渺小、太脆弱,无法体现宗教精神的超越性。千百年来,莫高窟各个洞窟的基本模型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山洞该大还是小佛像是多是少,壁画是简约还是精致。这一切都取决于人。这就是“基本模式不变+日积月累”的“莫高窟式”文化红利。唐代“观音、文殊、普贤四像”。 《文明:1030-1059当群星闪耀》的内页描述还有宗教精神力量的另一个特点:“长期不变的核心+末端不断变化”。宗教总是追求纯粹的源头,所以早期形成的一些文化元素是稳定的核心,比如领袖、圣地和一些长期不变的象征。但宗教在传播过程中要适应时代、地域的变化,非核心要素也要发生变化。以敦煌为例,佛菩萨的主要形象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如菩萨ys、神女、夜叉都有变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飞天。飞天先生是佛教天界的音乐家。佛经没有详细描述,所以给艺术留下了空间。因此,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最为生动、独特。曾经有人打过一个比喻。敦煌就像一辆公共汽车,一路行驶着。每个站点上下车的乘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公交车的风格。最终,车子的结构、材质、装饰都变了,但仔细一看,老司机释迦牟尼却没有变。这是稳定性和创造力之间的有趣平衡行为。宗教的精神力量还具有稳定性的品质。当一种宗教在某一特定地方确立了统治地位时,它往往会长期保持不变。无论世俗势力如何对抗,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必须相信同一个宗教。这就是精神信仰的极致稳定。我们继续以敦煌为例。相传这里开凿的第一个佛洞就是乐尊和尚。那是公元366年,敦煌的前任统治者是秦国。后来又有北魏、隋唐、吐蕃、唐各诸邑的归义军,以及张氏、曹氏的归义军。敦煌不断易主,但佛教信仰却始终如一,没有改变。即使在党项氏征服敦煌之后,当地人仍然信仰佛教,并继续在鸣沙山开凿石窟。而且,李元昊最终需要各种合法性来源来立国称帝,其中之一就是宗教。这一时期,大辽拥有五台山,北宋拥有汉传佛教祖地洛阳白马寺。然而,唯一的佛教布党项人的一张商业名片就是敦煌。因此,西夏人民后来称敦煌为“朝廷圣宫”,并十分重视。尤其是榆林窟第3窟的《普贤菩萨变》壁画美轮美奂,创造了唐代以来敦煌壁画的第二高峰。凭借宗教的精神力量,敦煌艺术拥有三种抵抗时间的工具:一是选择能够超越时间、不畏时间流逝的艺术门类;其次,它在不变的核心和可变的边缘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不惧怕风格的变化;第三,有一定的大学水平,不惧怕世俗政权的更迭。这或许就是敦煌文化能够几千年不断积淀的原因。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埋葬这么多文献呢?敦煌艺术虽然有抵抗时间的能力,但美的一部分敦煌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破坏性和固定性——7万多份文献被埋在莫高窟的一个洞里,直到1900年才再次出现。接下来的故事你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些珍宝的大量出现,吸引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罗斯人、日本人、美国人也纷纷慕名而来。他们从王道士那里收买、偷窃、抢夺。 5万多件文物迅速流散到世界各地,如今国内仅存约1.5万件。藏传佛教洞穴位置位置。敦煌内页的《文明:1030-1059当群星闪耀》对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实际上比我们今天旅行时选择看到的洞穴、雕像和美丽的壁画还要大。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埋葬这么多文献呢?先前这些士人,是因为党项百姓即将遭受袭击,当地百姓海带领洞窟内的经书保护好珍贵的资料。后来,一些学者认为还有其他可能性。首先,藏经洞的资料明显有偏差,最晚的日期据说是1002年,所以藏经洞的关闭时间可能早于1036年。其次,藏经洞刚开放时,里面的物品分类整齐,文献资料都用非常高档的丝绸包裹着,这些丝绸都是顶级的艺术品。如果要避免战争的混乱,我可能不忍心去修复。另外,入口处还有佛经壁画。看起来洞门已经被仔细的封印包裹起来,但又不像是因为战争而被封印的。那么经洞的本质是什么?史学界有一个更根本的解释:由于里面的佛经大多是残片,所以佛经很可能是当时一座寺庙的地图。我。藏经库仓库中,本寺所藏经书不全。和尚们想要完成佛经,就将必要的材料整理好,放置在这个藏经洞里。然而,无论怎样解释,学术界尚未得出结论。无论真相如何,这批文件的价值都不可低估。那么,这些埋藏了800多年的敦煌文献为何如此重要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文化本身的传承是连续的,但文化的载体往往是断裂的。当一些文件丢失时,就会导致学术空白。举个例子。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了解到“隋唐时期实行土地均等制度”。换句话说,土地是国家的财产,卡帕波波则分配给老百姓耕种。平民死后,土地归还,重新建立由国家分配。原理很容易理解,但我不太明白平地制度是如何实行的:唐政府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行政能力,能够在分完土地后归还土地?不仅我这个中学生不知道,就连历史学家也不知道,因为所有手头资料中关于唐朝平地制度的记载太少,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平地令是一纸空文,没有得到落实。但敦煌文献中的户籍资料中有不少涉及到家族制度的具体细节。比如,一个家庭有多少人口,姓氏,朝廷赐予多少田地,欠了多少钱,都记录得很清楚。有了这些信息,一个学术上悬而未决的重大案件就可以得到解决。再比如,进化论到底是什么?从诗歌到歌词的过程?没有人知道,就连宋朝人也不知道。他们看到的第一首词很特别,是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的文学作品。至于早期,长安教坊的《清平乐》、《浣溪沙》、《菩萨蛮》、《临江仙人》、《罂粟花美人》等歌词,无人知晓。敦煌文献中记载的“敦煌曲”有上千首,立刻填补了这一空白。举个例子。当时人们看到的第一首《菩萨曼》是李白的作品:“素林如大漠织烟,寒山孤翠。暮步入高楼,顶楼有人?”敦煌歌词中的《菩萨曼》顿时变成了另一种风格。鳞片浮在水面上,直到黄河水流过完全干燥。太阳出现了,北斗七星又回到了南方。我不能休息,我必须等到三更才能看到太阳。”没有任何规则或结构,只是一系列的誓言和誓言——我不可能离开你,也没有办法去想!事实上,同一个作者的同一部作品也存在渐进性渐进的问题。比如李白的《进进酒》中有一句话“古之胜景皆孤,唯饮留名”。一份敦煌抄本把前半句写成“诸古异象已死”。其实,“正版”是人们在印刷时才有的概念,因为印刷需要固定的文字来进行大规模的机器印刷,但在手写时代,人们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固定文字和是非观念。前者比较优雅,后者比较粗俗,同时也比较残酷和生硬。历史学家刘波认为后者更好,“是善而不雅。”李白的原始形象是仙女,但在敦煌版本中,醉酒的李白更加咬牙切齿,敢于说出严厉的话。还有很多例子:自隋代陆法言的“切”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韵》,中国音韵史上的许多谜团都被解开了;因为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大量的变文,这是当时说唱文学的基础,推动了中国通俗文学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任何一个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学术领域都因为敦煌文献的出现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基本的学术问题都因为缺少一条关键的信息而无法解决。一旦解决了一个关键点,整个问题就解决了。举个国外的例子。大英博物馆有一件珍品,名叫“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人于公元前196年雕刻的石碑。为什么这如此重要?因为它用三种语言写同一节经文,即古埃及象形文字、普通埃及人使用的文字和古希腊语。有了这个泥板,古埃及象形文字就可以被并行解释。因此,罗塞塔石碑的发掘成为解开古埃及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很多敦煌文献都有类似的功能。一张纸的碎片可以撞倒多米诺骨牌,引发连锁反应,解决许多基本的学术问题。什么是不重要的?敦煌文献的另一个价值在于,除了可以填补空白的主要文献之外,非重要的敦煌文献还有什么价值呢?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傻:不重要的文件自然盟友价值低!没有必要。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大学时代的老先生曾说,日本学者在1960年中国学者编印的《敦煌资料》中发现了数百处错误,难道是因为中国学者水平难吗?不完全是。主要是因为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看到敦煌文献原著,只能通过二手资料进行研究,而日本学者则远赴巴黎和伦敦去见原著。 《沙州都督府图鉴》(部分)。 《文明:1030-1059星辰闪耀时》页面内的图画有何不同?差异是巨大的。虽然经洞内发现的敦煌文献有七万多件,但大部分都与佛教有关。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官方和私人文件得以保存下来呢?为了例如,与土地产权相关的信息。事实上,这些材料原本是衙门保存的档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就失效了。但纸张在唐代非常重要,寺庙利用这些废弃档案的背面来抄写佛经。因此,敦煌文献中大量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法律史料被不完整地保存下来。那么这和没看过原著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衙门档案上往往有“文书日期”和县城名称等字样,但这些字样会影响和尚抄写佛经,于是和尚把这部分剪下来重新粘贴,这些字就贴在文书里面了。中国学者在翻阅、影印、拍照的二手资料中看不到这些信息,只能不厌其烦地自行核实。当日本学者去欧洲慕用灯光照射文档,他们可以立即清楚地看到文档的原始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中国学者找出数百个错误。读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什么?其实,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只是时间、地点的判断;当我们移开距离,站在更广阔的时空坐标上时,对一份历史资料的价值衡量可能会完全不同。中国人特别喜欢收集历史书籍。从孔子的删节春秋到司马迁、司马光、二十四史、通典、同治、文献通鉴,不间断的大部史书给华夏文明的子孙带来了强烈的自豪感。但正是因为收集爱情史书籍过多,才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历史学家何乙先生英迪曾经说过,当初他来到西方学习时,发现西方的教会档案堆积如山。一座教堂往往可以保存附近居民的相关资料数百年,但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资料。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太发达了。史书编成后,原始材料可能会被丢弃。比如,明朝修订元史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徐达将军从元朝都城得到的元朝十三位皇帝的实际记录。但《元史》成书后,这些记载都被烧毁了。为何被烧毁?当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所有元朝历史都认为明朝重要或者想让后代看到。 《孟姜女变文》(部分)。 《文明:1030-1059当群星闪耀》里面的图不过我觉得还有技术原因。如果我是《元史》的编撰者,知道以后不会留下这本《元史》了,同时工作又重,时间又紧,我该怎么办?我能不能把原书肢解,保留必要的部分,与其他材料混合,好好地粘贴在一起,然后再找人抄写一遍。毕竟,这是非常方便和高效的。因此,我怀疑《元世录》即使没有烧毁,在编撰过程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坏。这种方法来自于一个作家的本能——史书的编撰者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来编撰一部史书,他当然认为自己收集到了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精华。原始数据的价值是多少?就连我写稿子的时候,各种资料都摊在桌子上,但是一旦稿子脚本完成了,看着用的材料,感觉有点恶心。什么是编纂?你在保留和热爱某一部分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看重和破坏另一部分。保存和破坏发生在同一过程中。现在你应该明白敦煌文献的另一个价值了。它不仅保存了一些当时人们认为重要、不应该丢弃的文献,而且还帮助了一些当时人们认为不合适的文献。重要文献逃过了历史学家的剪刀和炮火,流传了800多年,向现代人类展示了它们辉煌的价值。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敦煌有一份文件,将家奴授予自由人。大意是:有些人因为修行不够,生生世世造了很多恶业,所以今生成了奴隶。我家有一个佣人,名叫载伊,工作了五十多年,从来没有偷懒过。于是,我想到了他的孝圣,就让他自由了。我做了一件好事,带来了很大的福报。使我家世世代代、子孙后代都远离疾病、远离灾难。神啊,请证明给我看吧!日月星辰,我无法改变!整合和校对“孩子们应该把书放回去”。资料来源:沙志录,《敦煌契约文献集》,江西古籍出版社,1998。《文明:1030-1059当星辰闪耀时》内页图画 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份文献的内容。主人显然是榨干了奴隶身上的最后一滴血和汗,然后将他送走了。他还解释说,这件事是他家族的一大功绩。难道一千多年前这样一个不仁、虚伪、贪图财富的富家子弟的面容不是突然浮现在脑海中吗?如果我们想了解当时本土生活的某个方面,这不就是信息吗?信息清楚吗?它比许多抽象的历史记载更重要吗?但这是当时sibil的一份普通合同文件。荣新江教授还谈到了他为什么热爱研究敦煌,因为他可以摆脱老历史学家的束缚,自由地审视历史:“敦煌文献是在敦煌藏经事件本身中发现的。但是敦煌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现在的判断。也许我们现在视为珍宝、理所当然的评论、情感、判断和结论真的是非常狭隘的,它们会损害无价之宝。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我会不要相信自己的信念,因为我可能会错。” 原作者/何安安编辑/张婷/杨力校对
1030年至1059年,北宋仁宗时期。此时的中国,宋、辽、夏各方在边境博弈中达成了微妙的战略平衡。缺乏马匹的宋朝创造了“以远近近”的新战术体系。范仲淹的“先忧天下之忧,而后享天下之乐”重新定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士大夫精神为何在此时觉醒?从刘墉街的歌词到永恒的杰作《岳阳楼》,文学创作为何在此时掀起一股变革的浪潮?宋朝与西夏的历法博弈如何体现技术背后的斗争强度?最近出版的《文明:1030-1059》一书讲述了中华文明在看似平静的30年里在多个层面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嘉佑二年,1057年,是中国科举史上奇迹般的一年。本期共有进士388人。苏轼、苏辙、曾巩、程浩、张载同榜。唐宋八位大师的一半都聚集在这里。”在近日举办的《文明:1030-10》《五十九年》新书发布会上,该书作者罗振宇打开了这段历史切片,聚焦于公元1030年至1059年北朝的“闪亮星辰”。 《挑战与解决方案》图书馆 这些成功、失败、半成功都是宝贵的财富。 “以下内容摘自《文明:当群星闪耀时,1030-1059》,文章中所使用的图画均来自书中。经出版社许可出版。”文明:1030-1059当群星闪耀》作者:罗振宇版本:中国地图出版社2025年11月杜纳行为何重要?1036,这一年,党魁李元浩擒拿一举占领了苏州、瓜州、沙州,垄断了河西走廊,切断了旧地名与同一地产的联系。这个地方因为这场战争,当地人惊慌失措地将大量文件藏在一个山洞里,然后封锁了山洞的入口。这个发现有多重要?可以说,几乎所有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领域都因为这批新材料而被改写。陈寅恪先生对此表示:“一个时代的学术必然有新材料、新问题。用这种材料来研究问题,是这个时代的新学术趋势……出人意料的说不入主流。”换句话说,在20世纪初,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如果不使用敦煌文献这样的新材料,在陈寅恪先生眼中就不属于主流。那么就让我们趁今年党项征服敦煌的机会来问问:敦化为何是重要吗?什么知识分子?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解释呢?我们今天所说的敦煌文化,其实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时间上连续的敦煌,即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另一部分是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另一部分则相反,是被打断的——1036年被雪封存的敦煌文献,一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两部分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先不间断地看一下敦煌。敦煌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岩壁中。从南北朝初年到元末,工匠们执着、雕刻摩崖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现存洞窟735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泥塑、彩绘佛像3000余尊。这么大的尺寸还没有被锁定或收费多年。路过的人们可以随时进来看看。怎么能说是被打断了呢?中国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有一个共同点:都位于险要要道上,靠近路边。例如,云冈石窟位于山西通往内蒙古的一条古道上。所谓“走西口”就是这条路。云冈石窟内还有一处古迹,名为“古路车辙”。龙门石窟尤其如此。地处两山对话处,沂水河夹在其间,犹如一道天然大门。因此,此地又称为“一阙”、“龙门”。古代是洛阳通往关中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石窟分布图。 《文明:1030-1059 当群星闪耀》内页描述敦煌莫高窟怎么样?它地处中原文明通往西域的门户。远古时代,商队走到敦煌,南过阳关,走丝绸之路南道;向北越过玉门关,走向丝绸之路的北线。因此,敦煌自然是一个交通枢纽。古代石窟为何要开凿交通要道?要知道,古人为了开凿石窟,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他们除了砍山、开洞、造像、绘画外,还要培训大量的工人。毕竟,建造一座石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他们在计划什么?目的不是搞艺术品,而是弘扬佛法,积累功德,自然选择人流量大的地点。只有让南来北往的商人和旅人才能看到这个功德一旦他们看到,它就会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敦煌莫高窟为何在元代之后数百年无人知晓?那么敦煌莫高窟为何在元代之后数百年无人知晓呢?因为敦煌已经不再是交通枢纽了。明朝觉得自己的势力无法延伸到西域,所以只封了嘉峪关。我不出来,你不进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贸易逐渐断绝。嘉峪关位于敦煌以东约400公里处。嘉峪关将敦煌隔绝在长城之外,敦煌成为周边部落羊群的聚居地。虽然清朝后来重新控制了西域,但敦煌却成为了一座普通的陆地城市,不再是交通枢纽。不过,莫高窟还在,想看的人可以随时参观。乙即使不看明清以后的时期,单看敦煌从南北朝到元代几千年的辉煌,也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如此多的战乱、朝代更迭、如此多的部落来来去去,敦煌莫高窟如何维护,继续在悬崖上凿洞造像,积累数千年的世界文化奇迹?毕竟它是宗教精神力量的象征。宗教的第一个精神力量就是超越性。因为我们要超越太空,所以我们必须建造一座巨大的佛像;既然我们也需要超越时间,我们就需要用佛像来追求永恒——这种艺术形式太渺小、太脆弱,无法体现宗教精神的超越性。千百年来,莫高窟各个洞窟的基本模型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山洞该大还是小佛像是多是少,壁画是简约还是精致。这一切都取决于人。这就是“基本模式不变+日积月累”的“莫高窟式”文化红利。唐代“观音、文殊、普贤四像”。 《文明:1030-1059当群星闪耀》的内页描述还有宗教精神力量的另一个特点:“长期不变的核心+末端不断变化”。宗教总是追求纯粹的源头,所以早期形成的一些文化元素是稳定的核心,比如领袖、圣地和一些长期不变的象征。但宗教在传播过程中要适应时代、地域的变化,非核心要素也要发生变化。以敦煌为例,佛菩萨的主要形象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如菩萨ys、神女、夜叉都有变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飞天。飞天先生是佛教天界的音乐家。佛经没有详细描述,所以给艺术留下了空间。因此,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最为生动、独特。曾经有人打过一个比喻。敦煌就像一辆公共汽车,一路行驶着。每个站点上下车的乘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公交车的风格。最终,车子的结构、材质、装饰都变了,但仔细一看,老司机释迦牟尼却没有变。这是稳定性和创造力之间的有趣平衡行为。宗教的精神力量还具有稳定性的品质。当一种宗教在某一特定地方确立了统治地位时,它往往会长期保持不变。无论世俗势力如何对抗,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必须相信同一个宗教。这就是精神信仰的极致稳定。我们继续以敦煌为例。相传这里开凿的第一个佛洞就是乐尊和尚。那是公元366年,敦煌的前任统治者是秦国。后来又有北魏、隋唐、吐蕃、唐各诸邑的归义军,以及张氏、曹氏的归义军。敦煌不断易主,但佛教信仰却始终如一,没有改变。即使在党项氏征服敦煌之后,当地人仍然信仰佛教,并继续在鸣沙山开凿石窟。而且,李元昊最终需要各种合法性来源来立国称帝,其中之一就是宗教。这一时期,大辽拥有五台山,北宋拥有汉传佛教祖地洛阳白马寺。然而,唯一的佛教布党项人的一张商业名片就是敦煌。因此,西夏人民后来称敦煌为“朝廷圣宫”,并十分重视。尤其是榆林窟第3窟的《普贤菩萨变》壁画美轮美奂,创造了唐代以来敦煌壁画的第二高峰。凭借宗教的精神力量,敦煌艺术拥有三种抵抗时间的工具:一是选择能够超越时间、不畏时间流逝的艺术门类;其次,它在不变的核心和可变的边缘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不惧怕风格的变化;第三,有一定的大学水平,不惧怕世俗政权的更迭。这或许就是敦煌文化能够几千年不断积淀的原因。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埋葬这么多文献呢?敦煌艺术虽然有抵抗时间的能力,但美的一部分敦煌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的破坏性和固定性——7万多份文献被埋在莫高窟的一个洞里,直到1900年才再次出现。接下来的故事你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些珍宝的大量出现,吸引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罗斯人、日本人、美国人也纷纷慕名而来。他们从王道士那里收买、偷窃、抢夺。 5万多件文物迅速流散到世界各地,如今国内仅存约1.5万件。藏传佛教洞穴位置位置。敦煌内页的《文明:1030-1059当群星闪耀》对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实际上比我们今天旅行时选择看到的洞穴、雕像和美丽的壁画还要大。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埋葬这么多文献呢?先前这些士人,是因为党项百姓即将遭受袭击,当地百姓海带领洞窟内的经书保护好珍贵的资料。后来,一些学者认为还有其他可能性。首先,藏经洞的资料明显有偏差,最晚的日期据说是1002年,所以藏经洞的关闭时间可能早于1036年。其次,藏经洞刚开放时,里面的物品分类整齐,文献资料都用非常高档的丝绸包裹着,这些丝绸都是顶级的艺术品。如果要避免战争的混乱,我可能不忍心去修复。另外,入口处还有佛经壁画。看起来洞门已经被仔细的封印包裹起来,但又不像是因为战争而被封印的。那么经洞的本质是什么?史学界有一个更根本的解释:由于里面的佛经大多是残片,所以佛经很可能是当时一座寺庙的地图。我。藏经库仓库中,本寺所藏经书不全。和尚们想要完成佛经,就将必要的材料整理好,放置在这个藏经洞里。然而,无论怎样解释,学术界尚未得出结论。无论真相如何,这批文件的价值都不可低估。那么,这些埋藏了800多年的敦煌文献为何如此重要呢?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文化本身的传承是连续的,但文化的载体往往是断裂的。当一些文件丢失时,就会导致学术空白。举个例子。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了解到“隋唐时期实行土地均等制度”。换句话说,土地是国家的财产,卡帕波波则分配给老百姓耕种。平民死后,土地归还,重新建立由国家分配。原理很容易理解,但我不太明白平地制度是如何实行的:唐政府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行政能力,能够在分完土地后归还土地?不仅我这个中学生不知道,就连历史学家也不知道,因为所有手头资料中关于唐朝平地制度的记载太少,以至于很多学者认为平地令是一纸空文,没有得到落实。但敦煌文献中的户籍资料中有不少涉及到家族制度的具体细节。比如,一个家庭有多少人口,姓氏,朝廷赐予多少田地,欠了多少钱,都记录得很清楚。有了这些信息,一个学术上悬而未决的重大案件就可以得到解决。再比如,进化论到底是什么?从诗歌到歌词的过程?没有人知道,就连宋朝人也不知道。他们看到的第一首词很特别,是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的文学作品。至于早期,长安教坊的《清平乐》、《浣溪沙》、《菩萨蛮》、《临江仙人》、《罂粟花美人》等歌词,无人知晓。敦煌文献中记载的“敦煌曲”有上千首,立刻填补了这一空白。举个例子。当时人们看到的第一首《菩萨曼》是李白的作品:“素林如大漠织烟,寒山孤翠。暮步入高楼,顶楼有人?”敦煌歌词中的《菩萨曼》顿时变成了另一种风格。鳞片浮在水面上,直到黄河水流过完全干燥。太阳出现了,北斗七星又回到了南方。我不能休息,我必须等到三更才能看到太阳。”没有任何规则或结构,只是一系列的誓言和誓言——我不可能离开你,也没有办法去想!事实上,同一个作者的同一部作品也存在渐进性渐进的问题。比如李白的《进进酒》中有一句话“古之胜景皆孤,唯饮留名”。一份敦煌抄本把前半句写成“诸古异象已死”。其实,“正版”是人们在印刷时才有的概念,因为印刷需要固定的文字来进行大规模的机器印刷,但在手写时代,人们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固定文字和是非观念。前者比较优雅,后者比较粗俗,同时也比较残酷和生硬。历史学家刘波认为后者更好,“是善而不雅。”李白的原始形象是仙女,但在敦煌版本中,醉酒的李白更加咬牙切齿,敢于说出严厉的话。还有很多例子:自隋代陆法言的“切”敦煌文献中发现了《韵》,中国音韵史上的许多谜团都被解开了;因为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大量的变文,这是当时说唱文学的基础,推动了中国通俗文学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任何一个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学术领域都因为敦煌文献的出现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基本的学术问题都因为缺少一条关键的信息而无法解决。一旦解决了一个关键点,整个问题就解决了。举个国外的例子。大英博物馆有一件珍品,名叫“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人于公元前196年雕刻的石碑。为什么这如此重要?因为它用三种语言写同一节经文,即古埃及象形文字、普通埃及人使用的文字和古希腊语。有了这个泥板,古埃及象形文字就可以被并行解释。因此,罗塞塔石碑的发掘成为解开古埃及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很多敦煌文献都有类似的功能。一张纸的碎片可以撞倒多米诺骨牌,引发连锁反应,解决许多基本的学术问题。什么是不重要的?敦煌文献的另一个价值在于,除了可以填补空白的主要文献之外,非重要的敦煌文献还有什么价值呢?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傻:不重要的文件自然盟友价值低!没有必要。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大学时代的老先生曾说,日本学者在1960年中国学者编印的《敦煌资料》中发现了数百处错误,难道是因为中国学者水平难吗?不完全是。主要是因为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看到敦煌文献原著,只能通过二手资料进行研究,而日本学者则远赴巴黎和伦敦去见原著。 《沙州都督府图鉴》(部分)。 《文明:1030-1059星辰闪耀时》页面内的图画有何不同?差异是巨大的。虽然经洞内发现的敦煌文献有七万多件,但大部分都与佛教有关。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官方和私人文件得以保存下来呢?为了例如,与土地产权相关的信息。事实上,这些材料原本是衙门保存的档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就失效了。但纸张在唐代非常重要,寺庙利用这些废弃档案的背面来抄写佛经。因此,敦煌文献中大量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法律史料被不完整地保存下来。那么这和没看过原著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衙门档案上往往有“文书日期”和县城名称等字样,但这些字样会影响和尚抄写佛经,于是和尚把这部分剪下来重新粘贴,这些字就贴在文书里面了。中国学者在翻阅、影印、拍照的二手资料中看不到这些信息,只能不厌其烦地自行核实。当日本学者去欧洲慕用灯光照射文档,他们可以立即清楚地看到文档的原始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中国学者找出数百个错误。读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什么?其实,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只是时间、地点的判断;当我们移开距离,站在更广阔的时空坐标上时,对一份历史资料的价值衡量可能会完全不同。中国人特别喜欢收集历史书籍。从孔子的删节春秋到司马迁、司马光、二十四史、通典、同治、文献通鉴,不间断的大部史书给华夏文明的子孙带来了强烈的自豪感。但正是因为收集爱情史书籍过多,才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历史学家何乙先生英迪曾经说过,当初他来到西方学习时,发现西方的教会档案堆积如山。一座教堂往往可以保存附近居民的相关资料数百年,但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资料。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太发达了。史书编成后,原始材料可能会被丢弃。比如,明朝修订元史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徐达将军从元朝都城得到的元朝十三位皇帝的实际记录。但《元史》成书后,这些记载都被烧毁了。为何被烧毁?当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所有元朝历史都认为明朝重要或者想让后代看到。 《孟姜女变文》(部分)。 《文明:1030-1059当群星闪耀》里面的图不过我觉得还有技术原因。如果我是《元史》的编撰者,知道以后不会留下这本《元史》了,同时工作又重,时间又紧,我该怎么办?我能不能把原书肢解,保留必要的部分,与其他材料混合,好好地粘贴在一起,然后再找人抄写一遍。毕竟,这是非常方便和高效的。因此,我怀疑《元世录》即使没有烧毁,在编撰过程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坏。这种方法来自于一个作家的本能——史书的编撰者花费了如此多的精力来编撰一部史书,他当然认为自己收集到了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精华。原始数据的价值是多少?就连我写稿子的时候,各种资料都摊在桌子上,但是一旦稿子脚本完成了,看着用的材料,感觉有点恶心。什么是编纂?你在保留和热爱某一部分的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看重和破坏另一部分。保存和破坏发生在同一过程中。现在你应该明白敦煌文献的另一个价值了。它不仅保存了一些当时人们认为重要、不应该丢弃的文献,而且还帮助了一些当时人们认为不合适的文献。重要文献逃过了历史学家的剪刀和炮火,流传了800多年,向现代人类展示了它们辉煌的价值。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敦煌有一份文件,将家奴授予自由人。大意是:有些人因为修行不够,生生世世造了很多恶业,所以今生成了奴隶。我家有一个佣人,名叫载伊,工作了五十多年,从来没有偷懒过。于是,我想到了他的孝圣,就让他自由了。我做了一件好事,带来了很大的福报。使我家世世代代、子孙后代都远离疾病、远离灾难。神啊,请证明给我看吧!日月星辰,我无法改变!整合和校对“孩子们应该把书放回去”。资料来源:沙志录,《敦煌契约文献集》,江西古籍出版社,1998。《文明:1030-1059当星辰闪耀时》内页图画 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份文献的内容。主人显然是榨干了奴隶身上的最后一滴血和汗,然后将他送走了。他还解释说,这件事是他家族的一大功绩。难道一千多年前这样一个不仁、虚伪、贪图财富的富家子弟的面容不是突然浮现在脑海中吗?如果我们想了解当时本土生活的某个方面,这不就是信息吗?信息清楚吗?它比许多抽象的历史记载更重要吗?但这是当时sibil的一份普通合同文件。荣新江教授还谈到了他为什么热爱研究敦煌,因为他可以摆脱老历史学家的束缚,自由地审视历史:“敦煌文献是在敦煌藏经事件本身中发现的。但是敦煌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现在的判断。也许我们现在视为珍宝、理所当然的评论、情感、判断和结论真的是非常狭隘的,它们会损害无价之宝。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我会不要相信自己的信念,因为我可能会错。” 原作者/何安安编辑/张婷/杨力校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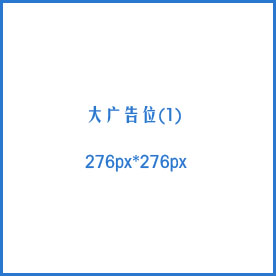
 推荐文章
推荐文章